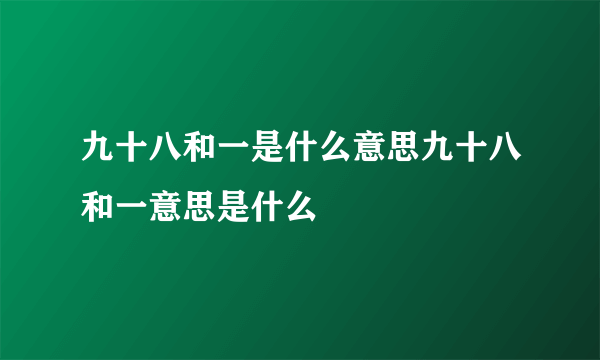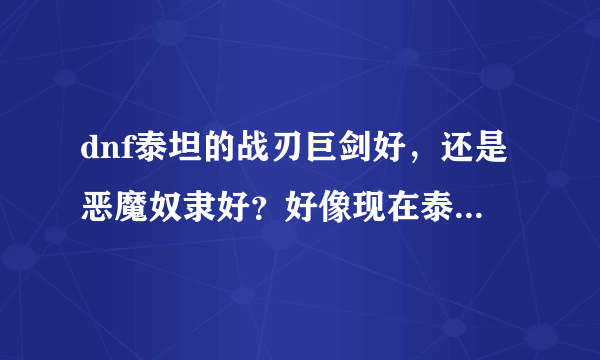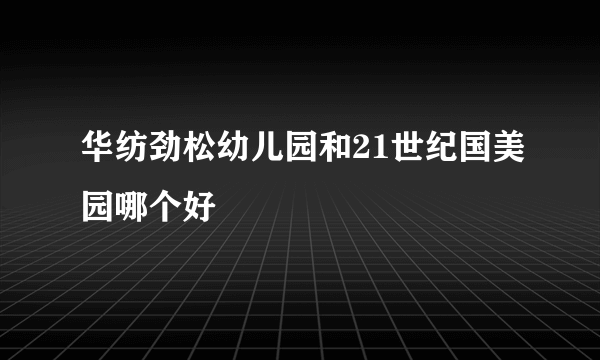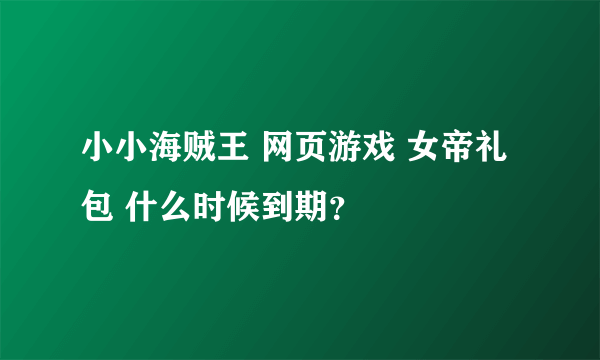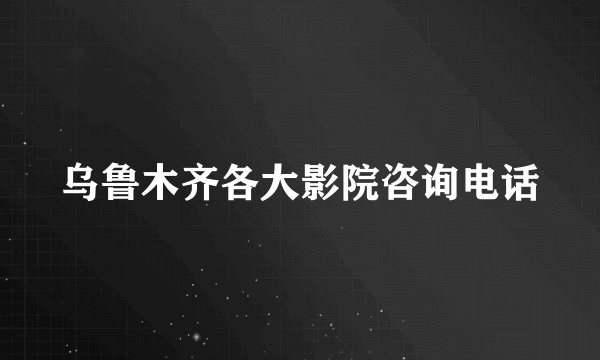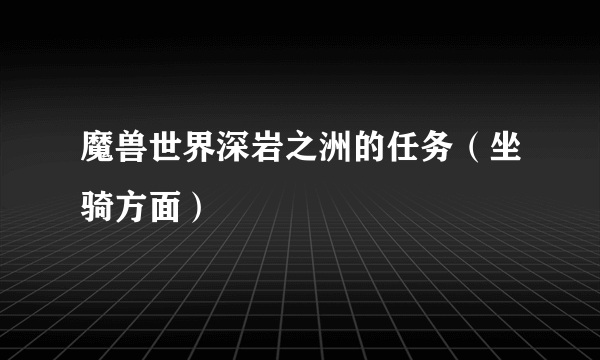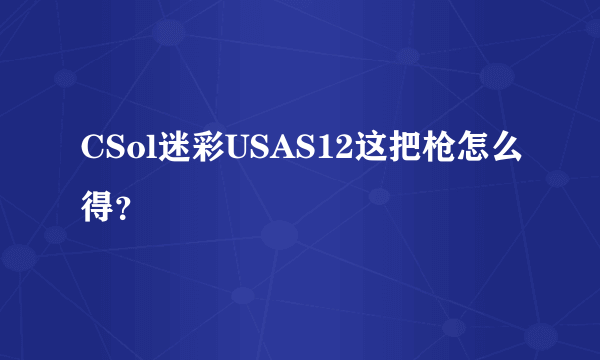太古的盟约的人物独白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人们对於强者总是抱持期待。
期待强者以轻描淡写的态度,解决复杂沉重的困难,并且不时颠覆传统,以压倒性实力挑战上位者的权威,以及,眨眼之间将仇敌轰成飞灰。
我是个强者,很久以前,很多次,我做过许多符合人们期待 ,所谓快意恩仇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很久以後——也就是现在 ,尽管我强者的资格有增无减,却已经无法说杀便杀、要斩就斩。
大部分时候,很多事情明明就是我轻松出手可以搞定 ,而我却偏偏必须犹豫好一阵子才有所动作,甚至犹豫之後不做任何 动作,很多人对於我踌躇不决的行为模式感到无法理解和谅解 ,批评我懦弱,不够果断,过於为他人著想。
我不在乎别人怎麼评论我,但我并不想欺世盗名,我必须声明的是 ,我……并不像你们所想像的那般善良。不管我告诉你们我犹豫的理 由是什麼,那都只是推托的藉口,实际上,我只是"不想管"而已。
为什麼?
因为我已经失去了兴趣。
曾经,我摧毁过最强悍的敌人、最凶恶的野兽、最蛮横的集团 、以及最坚实的堡垒。
但那又怎麼样?
也曾经,我见识过最高尚的情操、最伟大的英雄、最狠毒的阴谋 、以及最卑鄙的小人。
但那又怎麼样?
更曾经,我得到过最珍贵的秘宝、最锐利的兵器、最庞大的财产 、以及最惊世的武学。
但那又怎麼样?
我古老的灵魂历经了无数次大起大落与大悲大痛,当我救世的热诚以 及嫉俗的悲情被无尽的轮回所磨灭,难道我不该麻木吗 ?难道我不可以腻吗?
我找不出理由让自己再对那些所谓令人热血沸腾的事情感兴趣 ,所以我宁愿当缩头乌龟,所以我允许那些自大又无知的弱者在我面 前耍白痴、耍低能,所以我更放任那些居心叵测的能者 ,在暗地裏顺利推行他们筹画既久的阴谋。
想征服世界就去啊!
想奴役人类就去啊!
讲得难听点,那干我屁事啊……
我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极度无谓的心态有什麼不妥,毕竟我在这个世界 上经历过太多也太久,整个物质界的元素互相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运作模式我早已看透。我无法预知任何人的命运,但我会尽可能地 避免自己对任何人的命运造成重大影响——无论好人坏人 ,所有的成败悲喜我都不想参与。
我只想对自己负责。
说起来很轻松,但单单仅是那样,我已力有未逮。 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已经很久。
很久……很久……的……很久……
那是超乎寻常人所能想像的久,不过,我并没有见证这个世界的诞生,我不确定创世神是男是女,更不清楚鸿蒙初开时是否光明大战黑暗,我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事情一定有个开始,只是谁也不可能知道的更多。
但我知道的事情已经够多,好比说,兽人并不是这块土地的原生者。
兽人是我成年之後才出现的物种,他们的降临就像天外飞来的流星,毫无理由也毫无徵兆,以最野蛮的方式,取代了这块土地原本的霸主。
这块土地原本的霸主是龙。
是的,龙。一身亮片,咀嚼菸草,讲话像是含卤蛋,三不五时用尾巴挖鼻孔,在我的感觉里他们跟台客没有两样,是最俗不可耐的物种。
我很讨厌龙,年轻的时候宰过好几只,很多人无法理解独角兽怎麼屠龙?事实上很简单,我那支美丽的角可以是最慈悲的灵疗也可以是最致命的毒药,龙的心脏纵然比其他生物的心脏都强韧,仍然经不起我优雅的穿刺。
最初的那批兽人被後世称为原祖,在原祖降临之後,杀龙是一种常态,但是在那之前,杀龙是一件大事,除了会引来龙族的群起围攻之外,还有传闻指出必遭天遣。
许多没品龙找我寻仇,结果不是追不上我就是被我杀死,於是乎死在我角锥的蠢龙越来越多,其他灵兽甚至还为我起了「毒角裁龙者」的外号喝彩,显然龙族在这块土地上并不受欢迎。
当然,龙族不可能就这样随我耍著玩,否则他们没可能称霸这块土地,我的事情惊动了四方龙王,他们派出座下最得力护法「三头暴龙」对付我,那家伙的体型够我六倍大,三张嘴能吐冰、吐火、吐硫酸,最难搞的是还长了三颗心脏,我跟他足足缠战了半年,才在雪山之巅刺透最後一颗心脏。
但事情没有就此告一段落,三头暴龙拥有龙族祭师的资格,而且心脏够勇,临死前一边抽蓄一面向我发出诅咒,筋疲力尽的我根本躲不开,眼睁睁看著自己的身体硬化成金属,变成了一把兵器。
浑身动弹不得,神志却异常清醒,那种感觉十分无奈,大雪逐渐将我掩埋,想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见天日,我就不禁悲从中来,怀念本来的面目满腹心酸,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又变回了独角兽。
靠!原来这个诅咒是可以随我变的……
高兴当兵器我就变兵器,高兴当独角兽我就变回原形。
我不太清楚这个诅咒意义何在,不过我不认为三头暴龙诅咒我的目的会是为了赋予我变身的异能,当然我也怀疑三头暴龙会否因为跟我打了半年而日久生情爱上我,但那种剧情也太过无俚头,无论如何我很感谢三头暴龙,因为变成兵器就没龙认得出我。
之後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兵器的型态陷入沉眠,直到兽人降临,屠龙战役开始,我才故意躺到路中央让兽人捡去。
怎麼可以错过屠龙战役呢?多杀几只龙才不至於辜负三头暴龙的一番好意嘛。
◎◎◎
我的兵器型态是一把首尾双刃剑,握柄位於中段,顶端与末端延伸出刀刃,看上去就像是两把长剑一上一下绑在一起。
屠龙战争持续了几百年,我交接在一位又一位兽人英雄的手里,饱饮无数龙族的鲜血,而我可怕的锋利为我博得「凶极妖斩」的称号,我对於这些血腥一直没有特殊感触,直至切下最後一位龙王的头颅,莫名奇妙的厌倦感才占据我的心头。
当晚,兽人们大肆狂欢,庆祝他们终於完全称霸这块土地,趁著兽人疲睡,我变回本来面貌,远颺千里。
身为一匹有翼独角兽,张开翅膀,我可以飞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
直奔丛林最深处,我回到所有独角兽的故乡,我已经超过五百年没有见过同纇,他们就跟从前一样,伏在白杨树下,卧在鲜花丛里,对於这个四季如春的桃花源而言,外界就算杀红眼也影响不了任何一切。
同类们并没有欢迎我的回归,正好相反的是,他们竟然退避三舍!
我想是因为味道太重的缘故吧!兽人都臭的跟大便一样,跟兽人混了那麼久,我的身体闻起来一定好不到哪里去。
站在温泉池畔,我准备跳下去彻底洗个澡,望著轻烟缭绕的水面,一个令我震惊的倒影映入眼帘。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倒影。
那个我的倒影。
那个不是我
那不是独角兽雪白无瑕的倒影。
那是……斑马的倒影。
◎◎◎
我身上哪时候冒出这麼多条横纹?
我不解,但心里充满了羞耻。
独角兽是世界上最爱好乾净的生物,任何一丁点灰尘都不容许沾染,何况身体表面冒出这麼多圈愚蠢的纹路,还大剌剌游走在同类面前,实在丢脸死了,我满面通红跳下温泉,潜至最深处,又浮上水面,来回数十次,发疯般狂泳。
但无论泳姿如何豪迈,那些纹路的颜色依旧浑沌,丝毫没有转淡的迹象。
洗不掉是吧?好!没关系,老子跟你玩!在沙地上摩擦,在草丛里穿梭,甚至在泥泞里打滚,除了剥皮以外,可以作的我都试了,最後还招来闪电雷殛我自己,却通通都没用,这些纹路就像是束缚般不肯放过我。
当所有努力都徒劳无功之後,我反而冷静下来,我告诉我自己,如果不先理解这些条纹的本质,作再多尝试也只是耍宝。
我的精神沉淀到最稳定,灵识开达到最阔幅,物质界的诸般法相在这一瞬间全被稀释,只剩下灵波与磁场清晰无比,我看到重重血浪扑天盖地,我闻到腐臭的腥味冲霄而起。
我终於明白这些漆黑的纹路所从何来!
那是血痕。
是风干既久的血痕。
是由红转黑的血痕。
是我饱饮数百年的龙族血痕!
我听见龙族的哀嚎,看到龙族的怨恨,这一环又一环的血痕不是诅咒更不是报应,这些都是因果。相由心生,形於内而诸於外,反映我心境的转变,纪录我杀戮的岁月,擘画我身体的表面,忠实呈我的罪孽。
否定这些血痕等於否定我的过去,我不该那麼做,但是我选择那麼做。
耗费二十年的光阴,踏遍千山万水,我攀上天外天,渡过云之海,在物质界的边境找到传闻中能够净化元神的法宝「涤灵镜」。
穿过涤灵镜,我顺利回复本来雪白的面貌,而那些漆黑的条纹,则留在镜面的另一端孕育出一匹比子夜还幽暗的独角兽。
那匹独角兽自称为「貂朣」。
它说:它要永远跟著我。
永远…… 有些事情天生就不公平
天才与白痴,豪门与寒门,以及,男人与女人。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除了某些较为特殊的母系社会之外,体能上的劣势一直让女人屈居於男人之下,接受不平等的待遇,剥夺身为人类的尊严,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作为洗衣煮饭的奴仆,作为虚荣炫燿的陪衬,甚至,作为财产的一部分。
原谅我必须说的那麼难听,但,身为一个女人,对於男人长久以来的压榨当然会感到气愤,不过我也得承认,当世界以拳头论英雄的时候,女人成为弱者的代名词自然无可厚非,但幸好事情总会改善,工业革命之後,机器取代劳力,抢走了很多本来非男不可的粗重活儿,表面上,这项变革推动的是人类朝向更舒适的生活迈进,但在我的眼里看来,这是男女平权得以实现的伟大契机。
当男人不能够继续凭藉体能上的优势称霸职场,当工作条件对於体能的要求大幅度向下修正。
女人才真正可以站上与男人齐肩并行的起跑点。
我很高兴自己生长在男女平权的时代,虽然许多方面还有待加强,像是小孩都跟爸爸姓,像是嫁出去就不能回家吃年夜饭,不过,比起上个世纪又或者五十年前,女性的社会地位已经有了长远提升,最起码,我们跟男人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我的爸爸是国内有名的武术名家,我相信他一定很想生个男孩继承一身所学,但很可惜,我跟妹妹都是女的,虽然爸爸从来没有为此表露过遗憾,但我知道,他的心底必然怀抱某种程度的落寞。
我了解爸爸对於我们的爱不会因为我们的性别而有所增减,我也知道自己无论证明任何事都无法让爸爸得到慰藉,但我就是不想输给男生,所以从小我的功课考第一、赛跑冲冠军,就连在爸爸经营的武馆里,我这个所谓的大小姐比武也没有输过所谓的大师兄。
我告诉自己,长大以後绝对不靠男人,要作一个独立自主的成功女性。
不过,抱持那种理念并不代表我不需要男人。刚好相反的是,我丝毫不会否认伴侣的重要性,如果最後的结果是孤孤单单终老一生,那就算再怎麼成功也不会有意义。
很多同学无法理解为什麼我会喜欢图真,在他们看来,图真的身上没有任何优点可以赢过我。
那也许是事实,但过於表面。
让我们回归心灵基本面,问一个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到死还不明白的问题——女人到底要什麼?
要钱?要名牌?要美丽?要天天逛街看电影?
没错,那些我们都很想要,但是,当我可以自己满足这些欲望之後,我还要些什麼呢?
要一个老实可靠的家伙。
是的,梁图真,一个老实可靠的家伙。 我是语默。
我的个性就跟我的名字一样。
沉默并且孤僻,严肃并且冷静。
我讨厌废话,更讨厌多余的情感,我的脸上仿佛总是覆盖一层冰霜,让人难以接近,更拒绝让人靠近。
我的观念里有着明确的大是及大非,并且毫无疑惑的加以贯彻,我不需要为我的所作所为多加解释,我愿意为我所造成伤害负上全部责任,即使无法弥补、即便没有人认同,我仍然不会放弃自己秉持的正义。
月识族与生俱来便拥有读心的天赋,普通人无法对我们说谎,因为那样的缘故,我的族人普遍从事司法公职,我们济弱扶倾、看透隐藏在表面谜团下的真相,维护一般社会秩序,除此之外,也巧妙平衡太古遗族间各个势力的冲突。
太古遗族对这个世界能够造成的破坏是很可怕的,危机永远都在酝酿,事件随时都在发生,当状况扰乱到一般社会运作时,教廷就会出来制止。无数个世代以来,教廷以这种模式消弭了许多冲突,但也种下了许多不满,仇恨不断的在累积着,总有一天会一发不可收拾,造成人类与太古遗族的全面对立。
世界和平不能单单托付给教廷。
如果事情在教廷插手之前就能够解决,那么局势将会单纯得多。
看穿了未来的隐忧,从很早以前开始,月识族穿梭在各个族群间以各种手段安抚各种冲突。身为月识族下任当家预定人选,自懂事以来,我所受的教育不只要我学会如何领导我的族人,更要我学会如何协调各个族群。
为了让人类以及太古遗族双赢共存的局面持续安定发展,不论月识族还是我,都可以牺牲一切。
假若牺牲必须涉及其他人……那么,我将会慎重考虑。
曾经,为了达成目的,我欺骗并且牺牲过某个人。
尽管后来他安然无事,对于他的愧疚,我却没有一天能够停止。
出于无奈,一次又一次,我有意无意算计利用着他。
对此,他从未有过任何强烈反弹。
我无法看透他的思绪,但我知道他不在乎我对他的所作所为。
正因为如此。
当我发觉的时候,所有对他的愧疚,已经转变为好感,无法自拔……
※※※ 「没有力量的话,你什麼都不是。」
那是我妈最常提醒我们三兄弟的一句话。
我的两个哥哥名字依序是「大常」和「大胜」,而我的名字是「大军」,将来如果还有弟妹的话,那家伙的名字会是「大团」。
我们的命名模式透露出我妈对於胜利的强烈执著,一个女人能被外界评价为“死都要赢”,足以证明她的求胜心多麼旺盛,不过她并非天生如此,而是必须如此。我们家族是拥有跋厉族统治权的五大家族之一,彼此之间内斗激烈,我妈以一介女流之姿领导家族,如果没有令人敬畏的人格特质,早该被其他四大家族所并吞。
我承认她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但她绝对不是一个成功的妈妈或者妻子,不论我的爸爸还是我们三兄弟,每天睁开眼就是无止尽的锻鍊,永远都在为胜战作准备。
锻鍊的项目强人所难,往往都是超乎我们能力所及,做的好是应该,作不好就是该死,我的妈妈从来学不懂温柔与赞美,开口就是尖酸与刻薄。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就因为受不了她的蛮横而离家远走,我妈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我们都感觉得出来她很难过。
但我爸的离去并没有让我妈学到教训,事实上她变本加厉,除了严苛的修行以外,更要我们三兄弟搏命对打,像是仇人般互相杀伐。
我的年纪虽然最小,但我的斗气修为最高,因为我是焚海戟的天命传承使,就算躺著练也比大多数人吊著练强。我妈规定对战最输的那个人要接受处罚,所以我一直压抑著自己的斗气跟两个哥哥对打,如果不那样的话,他们没有赢的机会。
但这种小孩子的把戏又怎麼瞒得过我妈呢?
前几次她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後来她越看越火大,暗暗在旁边发招帮助两个哥哥对我进攻,那猛烈的攻势逼的我难以保留,彷佛猛虎出闸般全力激发,炸裂轰然巨响。
结果大常被我打瞎一只眼睛,大胜被我打成残废……
而那一年我才十一岁……
我好恨我妈为什麼要这样逼我。
我也恨我爸为什麼放我们不管。
所以我离开了那个家,所以我不想当太古遗族。
去你妈的跋厉!去你妈的焚海戟!去你妈的力量!
我什麼都不要!你听见了没有?霸爵欧蒂娜!
什麼都不是又怎样?我什麼都不要! 绝大多数外族人都以为我父母双亡,都以为爷爷膝下只剩下我,就连拓旡族本身,也有不少群众如此认定著。
但事实上——那纯粹是误传!
我完全不意外何来有此一说,虽然我不想承认,但,爷爷实在是非常致力於否定我父亲「岛田政广」的存在。
我的父亲毫无疑问是个好人,而且也非常努力,不过,十分遗憾的是,他的各方面能力都太过平庸,就算一天只睡一个小时刻苦修行,最後累积的成果,距离爷爷所要求「作为一个领导者的最低标准」仍然差之甚远。
在无数次考验挫败之後,爷爷下令褫夺父亲的继承权,并且视其为岛田氏的耻辱,除名於族谱之外。而在我出生之後,父亲更被外放到邻国掌管规模简陋的分公司,永远地脱离家族权力核心。
我不难谅解爷爷用心良苦,当世第一大族的首酋之位当然要委贤以任,不过,我不能茍同爷爷对於父亲的排挤,甚至勒令父亲不得与我接触,就好像父亲身上罹患某种无药可救的传染病一样。
当然,这件事情毫无我干涉的馀地,站在爷爷面前,除了点头称是以外,我不被允许表达其他意见。
我只有接受的义务。
从懂事开始,我就被关在一间两百多坪的房间里,各门各科最好的老师轮流帮我上课,除非完成爷爷指定的精英基础课程,否则我终生没有踏出门外的权利。
这个房间不但是最完备的教室,也是最严密的监牢,而我更可能是拓旡族史上年纪最小身分却最尊贵的囚徒,文武繁重的课程压的我喘不过气,所有关於外界的知识都只能透过教材取得,我没有摸过任何一团泥土,也没有看过任何一片天空。
我幼小的心灵渴望自由,四岁那一年,我竭尽所能耗费一个月的时间,在不被发觉的情况下挖了一个地道想逃走,但是我失败了,双手挖到指甲翻脱仍然不见天日。
後来我才知道,自以为秘密的潜逃行动其实都在大人的掌控里,而他们不动声色,只因为那个房间位於两百公尺深的地底。
想挖出去根本是个笑话。
在那段紧绷的童年里,我不被允许消遣或娱乐,只能专注於修行与学习,所有的课程都是那般地烦闷和枯燥,只有间谍卫星所拍摄的阿姆雷特生活纪录,可以稍稍纾解我的脑神经。
是的,欧大军。
这个注定要跟我分出胜负的焚海戟传承者。
这个天生叛逆的没水准粗俗人。
虽然同样也生长在被逼迫的环境里,但是,我很羡慕他。
羡慕他可以在草地上打滚,可以在沙滩上狂奔。
羡慕他开心的时候高声嘶吼,悲伤的时候涕泗纵横。
看著他直来直往的生活花絮,有些时候,我会觉得,永世战争的胜负并不是那麼重要。
有些时候,我会觉得,爷爷还有各位老师的教导也不是那麼值得挂心。
真正重要的是……
真正值得在意的是……
我……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阿姆雷特。
拜托……
一句也好…… 过去就像一首歌,有事没事都被人们哼著唱。
想着想着,梁图真的脸上开始不自觉的微笑。坐在他身边的关晓蕾,看到这种情况,很是疑惑的问道:“图真,你在发什么神经。”
“去!谁跟你发神经!”梁图真比个郑重的手势道:“我告诉你喔!这个人生啊……”
“人生怎么样?”关晓蕾手撑着头,眼睛眨了眨说道。
梁图真清清嗓子,正经的说道:“就像是一盒火柴,对它处之太郑重其事,是愚蠢的;但是如果忽略它,则又太危险。”
“所以呢?应该要怎么做?”
梁图真想了想,摇头说道:“我不晓得!”
关晓蕾有点哭笑不得:“那你刚才讲的那些不就都是废话而已。”
“当然不是!”梁图真望向窗外,煞有其事的喟道:“只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是不会有标准答案的。”
关晓蕾微笑的说道:“因此我们只要提出疑问就好?”
“没错。咦!你怎么会知道?”
关晓雷没好气的说道:“因为你很久以前就告诉过我了,还说什么每一件事都是注定的。”
单纯的男子意外的讲道:“没想到你记得很清楚嘛!”
“普通啦,你现在还是认为一切都是注定的吗?”
摸了摸口袋里忘了拿去给关老爷的玉板指,梁图真忽然心有领悟,淡淡的说道:“是的,都是注定的……”连带我跟你在内,一切都是注定的…… 隔了一年才交出这集,我的脸皮也算够厚的了。
所有还愿意等待这部故事的朋友们,请接收我的最敬意,也许你们日夜诅咒我,但我希望你们了解,我实在很抱歉。
如果要选出一个字描叙过去这一年,我会选择“空”。
因为去年是我放空的一年,乏善可呈也乏咎可悔,六月底把工作辞掉,起初的理由当然是想要专心写稿,看看能不能走啊日结束这故事,稿没写多少,钱倒是花光了。
做吃山空,这真是一个悲惨的警示物语!
算啦,大过年讲这些丑事大不吉利,我们谈谈这一集吧!
有看过试阅的老朋友多半会抱怨:怎么梁图真后半集才登场,这个问题从第一季开始就常常被读者拿出来鞭,那也不能怪我,谁叫他是无敌的角色,一天到晚只会破坏战场平衡,场景跟着他跑的话,根本没几场战斗可以写。
你们大概有注意到梁图真一直是以耍白痴居多,而我也注意到你们很喜欢看他耍白痴,其实要让他贯穿整本书也不是不可以,我有很认真考虑从善如流,毕竟这本书是你们在看,我的意见并不是很重要,也许第十集会试试看吧,只是那样一来,《太古的盟约》就会变成名副其实的搞笑书。
并没有很多人批评我的文笔,但会挑剔的人都是针对同一点——代名词用太多,以至于看得很辛苦。改善这个缺失成为这几集最大努力方向,到了本集可以说已经大功告成,不知代名词变少,古名跟俗名也只择其一运用,相信不会再发生眼花缭乱的问题。至于很喜欢代名词的读者们,请多见谅啰,简化之后比较没负担。
剧本创作有所谓的三一论,也就是时间的统一,人物的统一,以及场景的统一,小说虽然不是剧本,但我一向不喜欢快速分镜的故事,这集算是特例,到处跑来跑去,出国也就算了,还跑去不同世界,大违我的创作理念,可幸的是最后又把梁图真拉回校园,他已经好久没有回到这个场景,毕竟是个学生会长嘛,怎么可以不务正业呢!大家也希望他帮晓蕾多分但一些杂物是把!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会努力提升写作速度,也加快故事节奏,我知道你们对我感到失望,但请不要绝望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