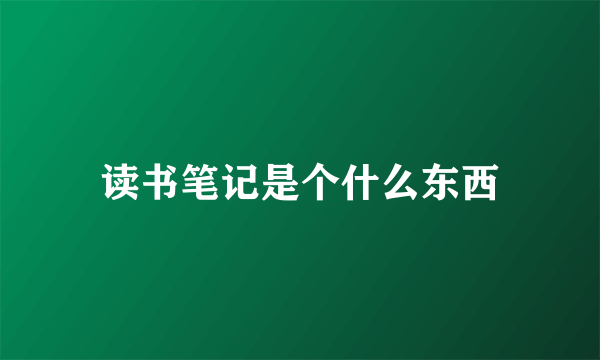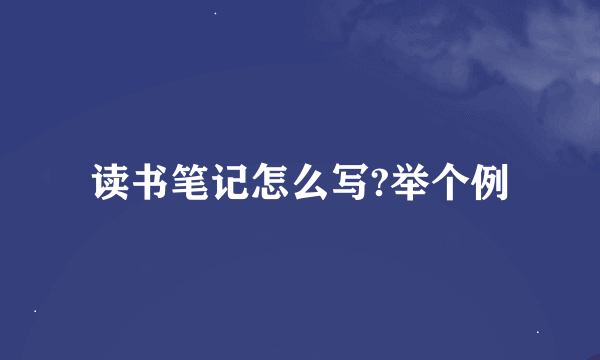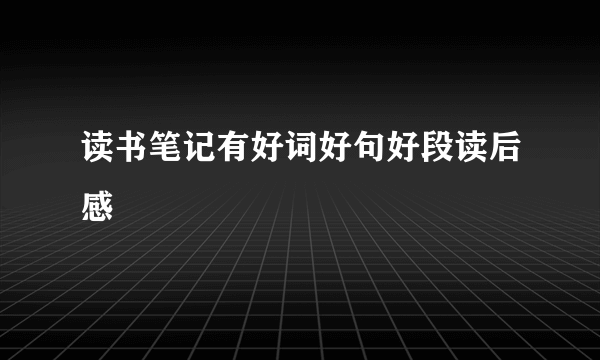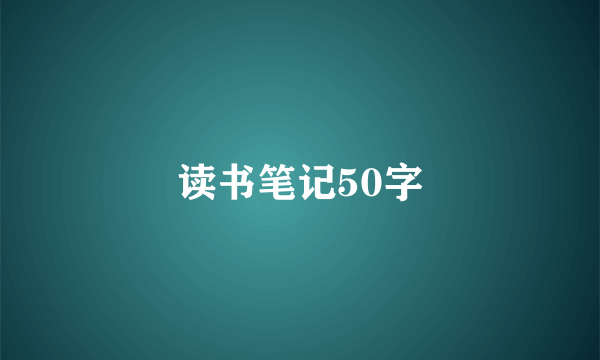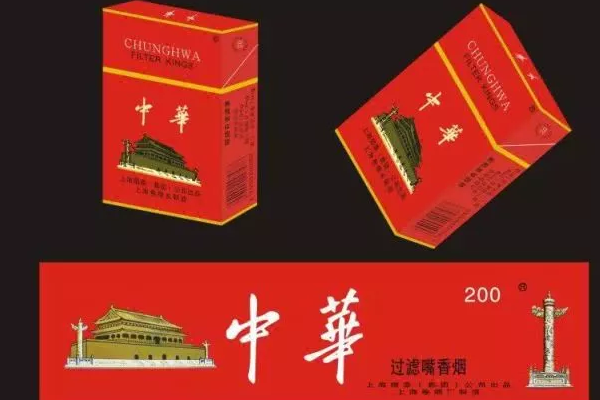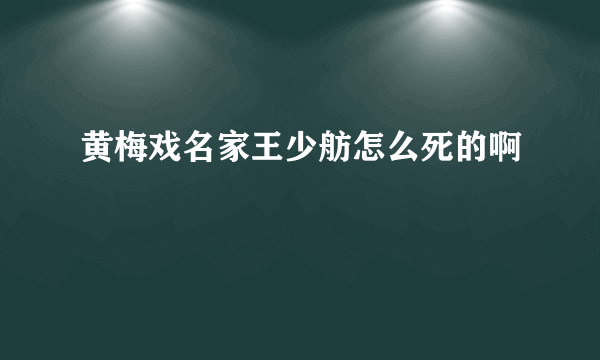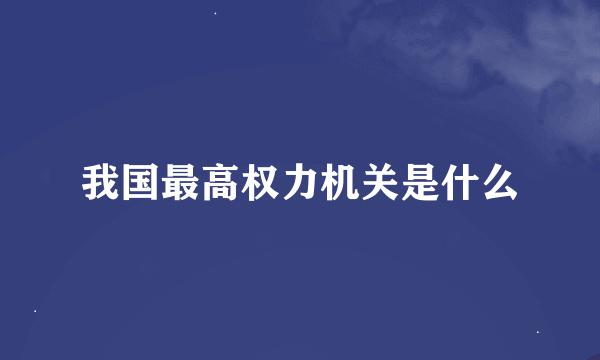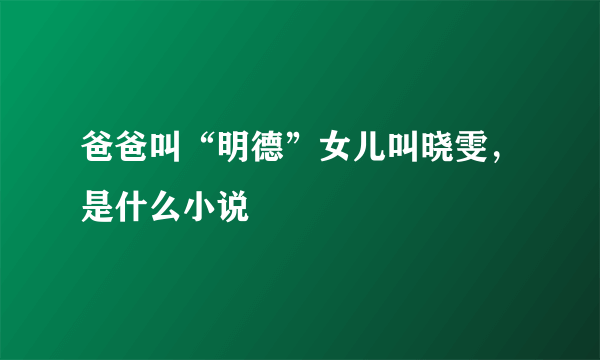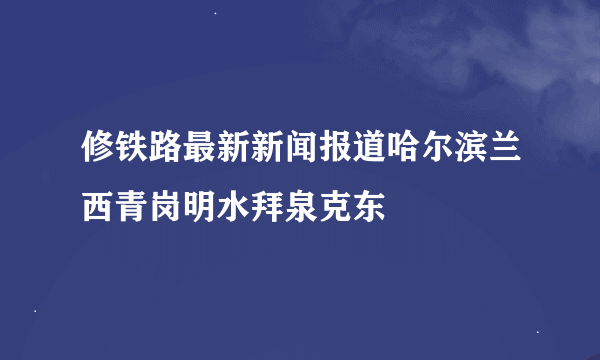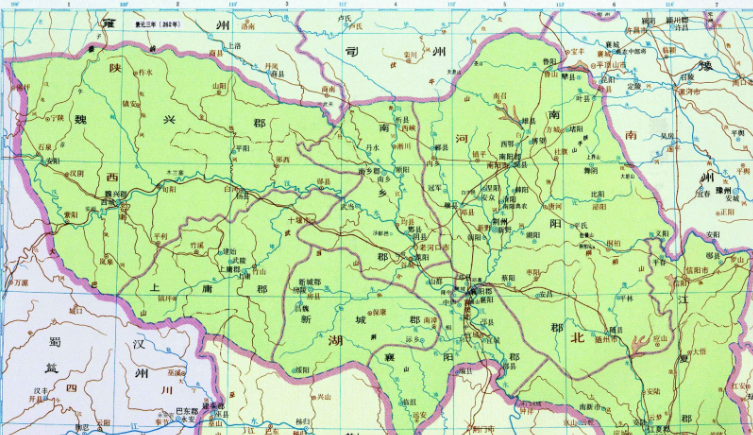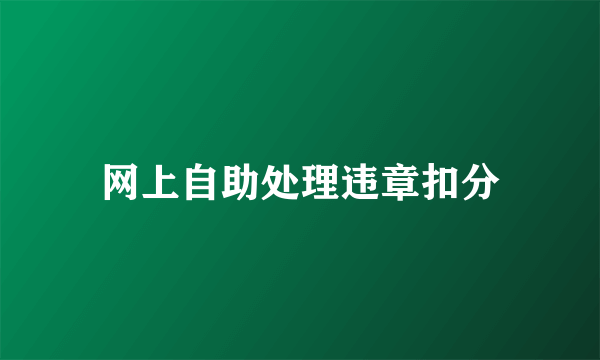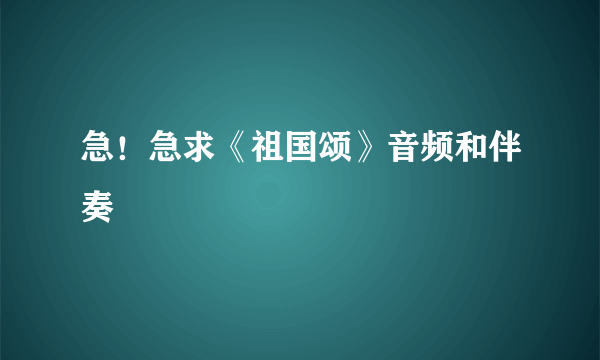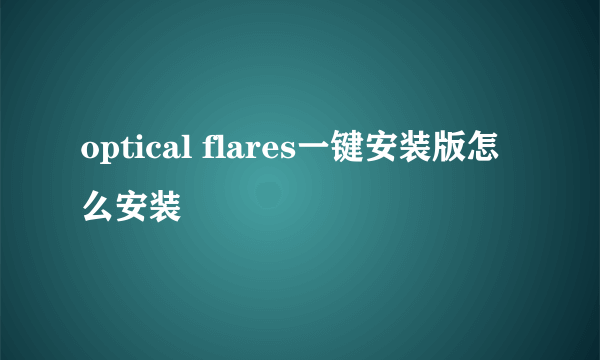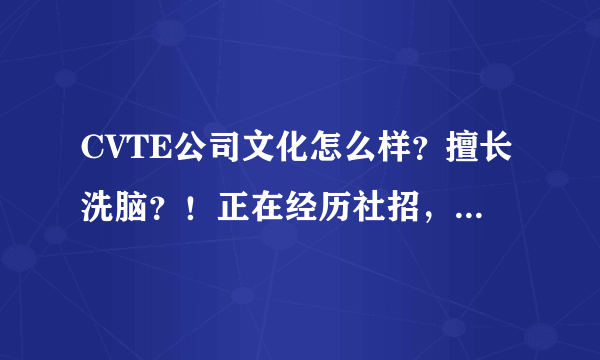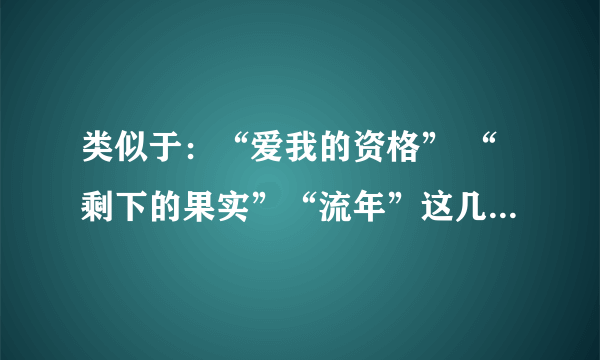悲惨世界读书笔记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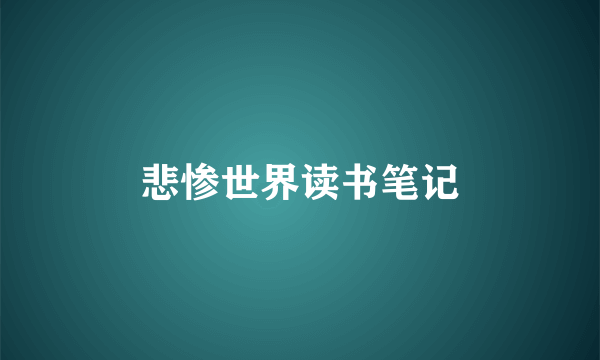
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发展心理学家柯尔伯格对皮亚杰的品德发展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再证实工作, 运用道德两难问题进行长期追踪实验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自己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把道德发展分为六个阶段,分属于三种不同道德水平.下面结合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著作《悲惨世界》中的主要人物对这一理论进行分析. 《悲惨世界》以1815年拿破仑失败,1830年复辟王朝覆灭,巴黎人民举行起义推翻七月王朝这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生动地描写了十九世纪前期法国劳动者因事业和贫困而遭致堕落毁灭的悲惨生活图景.文中体现的社会道德问题亦十分具有代表性与集中性. 作品的主人公冉阿让,在一家人濒临饿死的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用拳头打破面包店橱窗抓走了一块面包,因此被捕,判了5年苦役.其间,冉阿让因极为担心家人的生存而几次越狱,但无一成功,反被加刑至19年.主人公冉阿让的这一小段经历中,已包含了两个”两难”的境地.看一下他自己的想法吧:他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无罪的人,但他是在愿意工作而没有工作,愿意劳动而又缺少劳动的情况下走上犯罪的道路的;他认为法律对他的处罚太重了.他的结论是:他所受的处罚,实际上不仅是不公允,而且肯定是不平等.他认为不仅社会有罪,上帝也有罪. 在这一时期里,冉阿让背负着全家的生计,是具有强烈责任心和义务感的,所以他才会冒着风险去打破商店橱窗拿走面包以延续家人的生命.同时他又是注重社会契约关系的,从他承认自己不是个无罪的人这一点可以看出.然而权衡利弊,他选择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做法一一偷面包.在他的观念中,社会一向是强调生命的重要的,濒临饿死的人要求得到食物的权利,重于一块面包的价值.两者相衡,冉阿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其偷窃行为纵然是违法的,但也是符合道德意义的. 在这一阶段,以柯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论而论,冉阿让的道德发展水平已处在了第五阶段:社会契约定的向阶段. 接着看作品.冉阿让年值46岁时刑满释放,带着标志着苦役犯身份的黄色身份证,因此走遍了所有的旅馆,店铺和酒店,没有一个地方肯收留他.经人指点他来到当地主教米里哀家中,说明身份并且只提出了极低的住宿要求.但米里哀却款待了他,并且在他偷走一篮银质餐具被警察扭送至主教家对质时,仁爱的米里哀却非但没有责怪他,反把那些餐具与另一对银质烛台都送给了他.冉阿让仓皇出城.他在惝恍迷离的心境中用脚踩住了一个穷孩子掉下的钱,孩子找不到钱哭着走了.冉阿让因此后悔莫及,他经历着痛苦的思想冲击,决定选择一条自新的光明之路,从此重新做人. 这里出现了矛盾两方面的激烈冲击,一是米里哀主教极度的宽大仁慈,一是冉阿让因长期受这个污浊不堪的社会氛围影响而形成的不良作风.但他最终清醒了,他按他的良心所选择的道德原则来进行道德判断,挣脱了现实社会所谓”规范”的限制,他由于”惯性”与当时极为不安的情绪而犯下错误,所以在他认识到自己错了之后,产生了强烈的内疚感和自我谴责感.通过以上的分析与论证,我们可以看到冉阿让在此时,已进入了道德发展的第六阶段,即良心或普遍道德原则的定向阶段. 故事发展到这里,主人公冉阿让便已经开始了他的新生.他改了名字,发展工业,并不惜一切代价做各种善事,还当上了市长,被人们尊称为”马兰德老爷”.但故事到这里又有了波折:一名工人被误认为是冉阿让而即受审,这让冉阿让内心起了剧烈的矛盾斗争:如果不闻不问此事,那名工人便会成为他的替身去监狱受苦;他的”马兰德老爷”的身份就更无人怀疑了.但是,他的良心不允许自己这么做.最后他选择了自首,用自己的终身监禁换取无辜工人的自由.然而自首后,冉阿让又越狱了,因为他还要抚养一个命运悲惨的女人芳汀留下的女儿珂赛特,他还有很多善事要做,最关键的,应该是他对这种不平等社会契约的强烈反抗. 经历无数事情之后,冉阿让的品德内化过程已经达到了信奉的水平.他作出选择的驱动力是自己的价值信念,而不是物质力量,也不是外在压力如社会对他隐瞒身份的议论和法律即将给予他的处罚.冉阿让后来又经历了入狱与逃跑,最终还是把珂赛特抚养长大了,虽然这其中有太多暗流般的惊心动魄. 一个出身贵族的青年马吕斯,与貌秀美的珂赛特产生了爱情.他们冲破众多外在的阻碍最终得到家族对他们婚姻的认可,冉阿让在其中也起了重大的作用.这时冉阿让对马吕斯道明了真实身份,而马吕斯却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冉阿让是个屡犯窃案的罪犯,竟要冉阿让离开他家,冉阿让只得带着无奈与伤痛出走. 马吕斯看得到冉阿让平时的言与行,也能从珂赛特良好的教养与可爱之中体会到冉阿让品质的高尚,但他仍认为冉阿让是十恶不赦的罪犯,或者是因为他认为罪犯就是可耻的,没有任何辩驳的余地,或者是因为他认为贵族的家庭无法容忍一个苦役犯,总之他要求冉阿让离开.所以可以看出,此时的马吕斯的道德发展水平还处于相对低下的第三阶段:人际和谐的定向阶段.马吕斯要求冉阿让离开,是基于当时整个社会风气的,他以遵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和习惯角色行为为规范,根据别人是否接受或赞赏自己的行为为判断准则.当时人们普遍不接受苦役犯的状况在前文已有介绍,那么,这个出生于保守贵族家庭的年轻人更不可避免地受到风气的强烈影响.然而后来,马吕斯从别人口中知道了冉阿让不仅是珂赛特的恩人,并且还曾经几次救过自己的性命。他为冉阿让的道德精神所感动,与珂赛特一同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冉阿让,冉阿让最终在年轻的夫妇的臂弯中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 故事到这里便是终结,人物道德水平发展也有了定格。冉阿让,受尽了剥削,压榨,歧视与法律迫害,但他的离去却伴着微笑。他对这个世界宽容了,或者是他得到了世界的“宽容”。以仁爱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道德原则在冉阿让的身上逐步体现并最终定性,这帮助他超越了社会的现实也超越了自我;马吕斯,一个年轻的贵族,经理颇多但却单一,险些成为社会旧传统的牺牲者与拥护者,然而冉阿让的仁爱的道德精神让其感动,可以说他的道德发展阶段从前习俗水平跃升到后习俗水平。 对冉阿让和马吕斯两个人物进行分析之后,还得说一下一个不得不提到的人物:警官沙威。 警官沙威绝对是一个令人战栗的人物。在冉阿让还是“马兰德老爷”时,这个警探便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他还逮捕了上文提到过的时为妓女的命运悲惨的芳汀,其理由是“一个娼妓竟敢冒犯一个绅士”。目睹了事情真相的冉阿让命令沙威放了芳汀,然而沙威释放芳汀,也并不是出于对事件做出了公允的判断,而是迫于时任市长马兰德也就是冉阿让的权威。沙威此类的举动中,最多的便是对冉阿让身份的怀疑,并一直试图抓住这个苦役犯。他这一系列的行为,明确地显示出他的道德发展阶段处于维护权威和秩序的定向阶段,在他的思想中,法律和权利至高无上,他相信社会秩序由准则和法律在维护,服从团体规范、严守公共秩序、尊重法律权威并接受和遵从社会和他人的期望。逃犯是为法律所不容的,无论理由如何,法律的权威必须维护,否则社会秩序就会紊乱。 然而沙威的最后一次出现,却是他的死亡,原因是他有感于冉阿让的仁爱,一反既往没有逮捕他,而在放走他之后,陷于职责和道德的两相矛盾中,投河自尽。 沙威的自尽,标志着他德意识的自觉。他终于意识到了国家机器与社会习俗加在他身上的桎梏,这桎梏却无法摆脱,但他的道德水平却有了质的提高。 以上为整部作品主要人物道德发展阶段的纵向分析。综合三个人物在小说中体现出的道德发展情况,如下所示: 冉阿让: 社会契约定向阶段 → 良心或道德原则定向阶段 马吕斯: 人际和谐的定向阶段 → 良心或道德原则定向阶段 沙 威 : 维护权威和秩序的定向阶段 → 良心或道德原则定向阶段 可以很容易地看到,道德发展的顺序是一定的,不可颠倒的。再作仔细的比较,冉阿让在社会契约定向阶段停留的时间较长,沙威却在冉阿让的感召下迅速从第四阶段上升到了第六阶段,而马吕斯几乎可说是没有在第四和第五阶段停留。 然而他们终归上升到了最高的也是现今社会最为期待的第六阶段即良心或道德原则定向阶段,究其原因,竟是出奇的一致:受到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的感化。感化,让受事者把外在的刺激内化为自身内部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又使受事者本身以其为原则或标准产生自律行为。马吕斯从小遵守的是严格的家教和贵族的规则,他甚至都不明白为何要遵守这些原则,然而受冉阿让感化后,却以仁爱为原则,去爱冉阿让。这很明显地体现出了人类的道德教育认知发展是从他律到自律的。再看沙威,我们不得不说他是一个悲剧,一个因道德发展状况不佳而产生的悲剧。沙威在第四阶段的长期停滞,已经给他所在的社会造成了许多的悲剧,同时也在为他自身的悲剧一点一点积下沉淀。(我们要注意的是,处在第五阶段的人们虽尊重法制,但更会权衡利弊,所以会认为社会契约和法律不适合社会发展时应被即使修正。而第四阶段的人却只是一成不变地维护法律的权威,在现在这个法律尚不够全面,不够人性化的社会中,这一阶段的道德准则无疑是冷酷的,甚至是可怕的。)长期的社会惯性已经把沙威的人格异化为国家机器中的一个小小的零件,当他重获人的道德认识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道德与职责的极端矛盾。也许有人会认为,如果冉阿让不出现,沙威也就不会自尽,也就不会成为悲剧了。但这种观点却是相当浅薄的,沙威自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他的觉悟,而在于社会对他的异化,而且,如果他不觉悟,他将给这个社会带去更多悲剧。从沙威的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到,道德培养的失败,对于一个人、对于整个社会造成的危害是多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