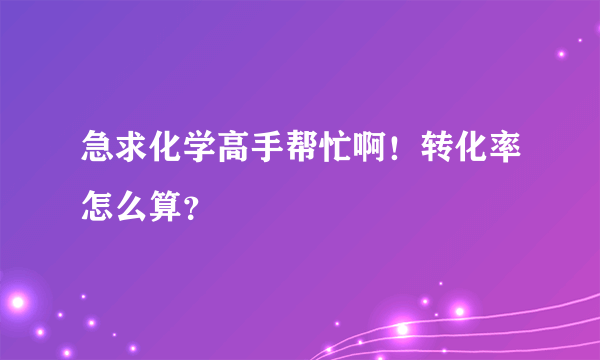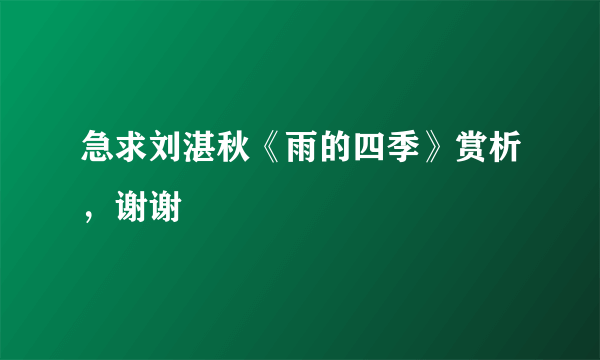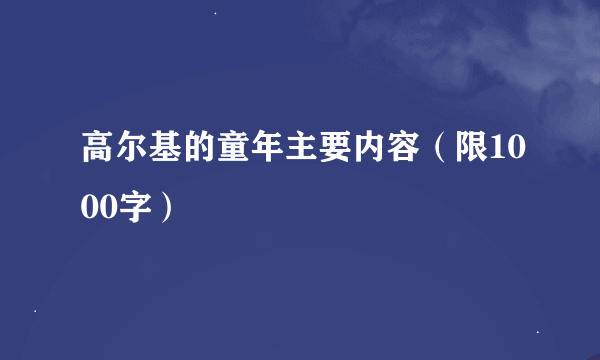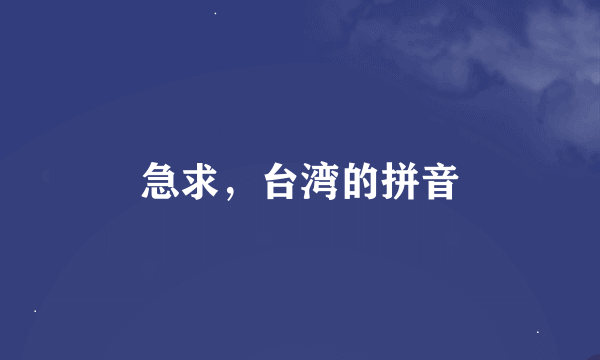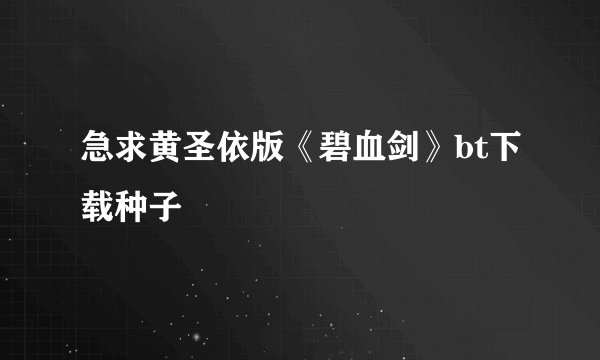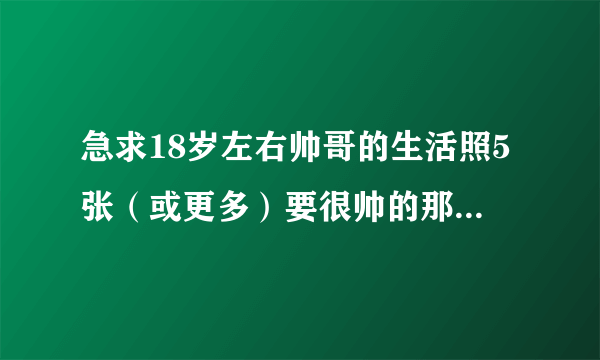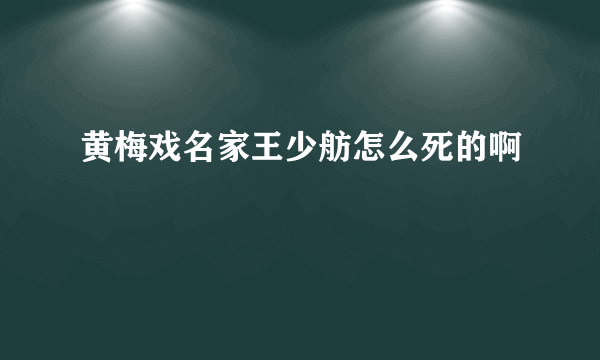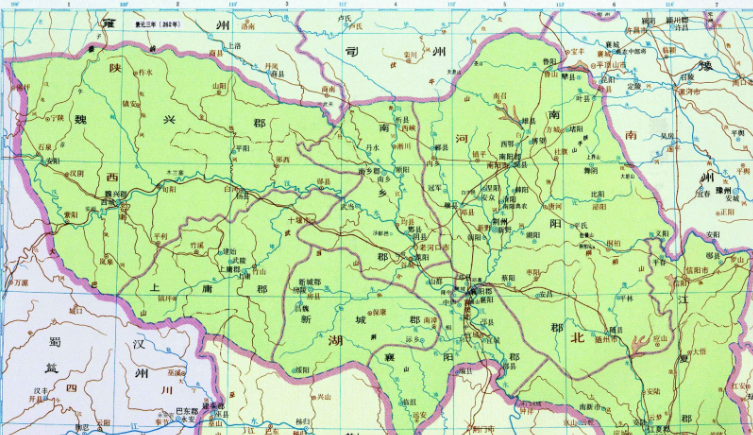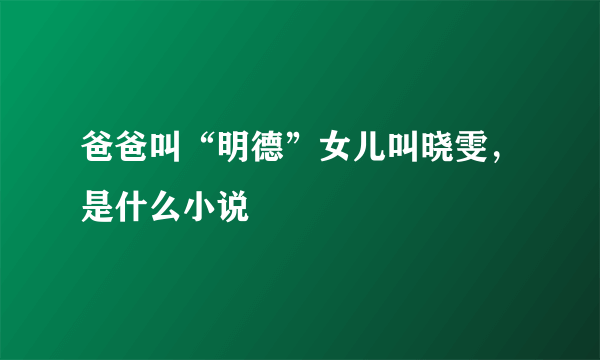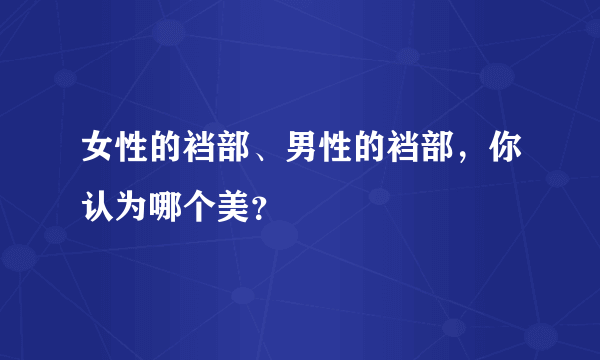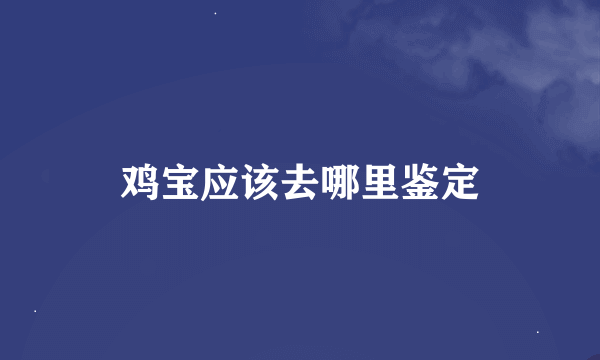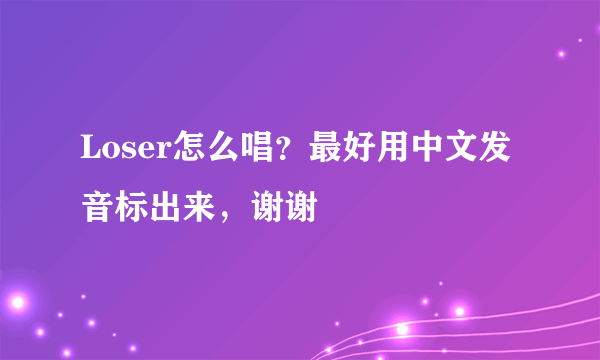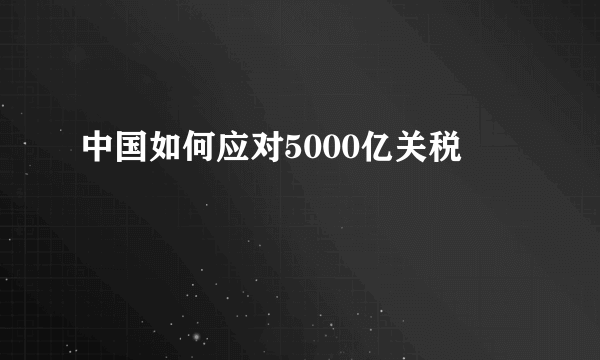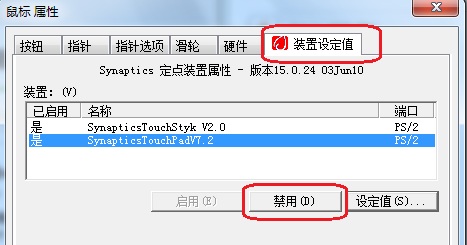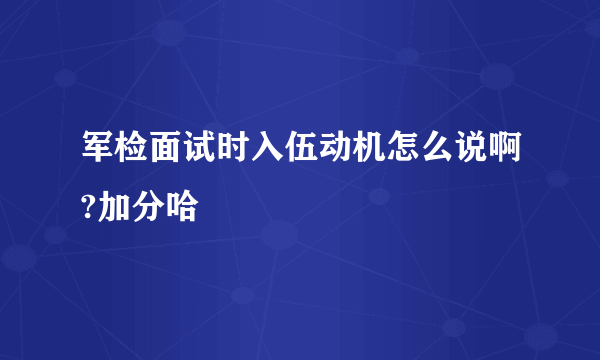急求五个高尔基的《童年》精彩片段!!!!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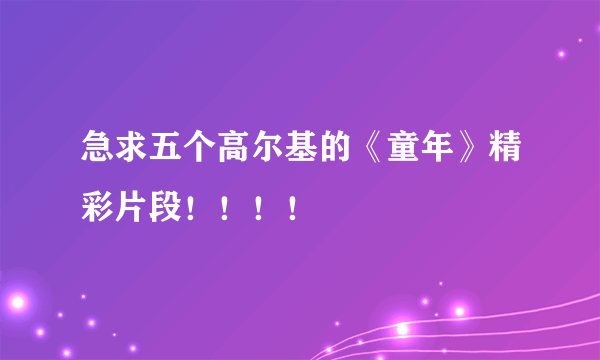
我的确很爱伊凡,他的精彩游戏常常使我惊愕不已。 每逢礼拜六,外公把一周来犯过错的孩子挨个揍一遍,就去做晚祷了。这时,厨房里就开始了非常精彩的活动,好玩极了。小茨冈从炉炕后面捉了几只黑油油的蟑螂,接着,他飞快地用细线做成马具,用纸剪一架雪橇,不一会儿,四匹小黑马就拉着雪橇在刨平的米黄色桌面上奔跑起来。伊凡用一根细长的木片驱赶着他们,眉飞色舞地尖叫道: “哎,去迎接主教啦!” 接着他又剪一个小纸片,贴在一只蟑螂背上,让它去追赶雪橇,一面解释说: “忘记带布袋啦,这个修士背着布袋追上去!” 这时,伊凡又用线栓住另一只蟑螂的腿,于是这只蟑螂低着头朝前爬去。伊凡拍手叫道: “这是教堂执事从小酒馆出来,现在去做晚祷啦!” 接着,小茨冈又拿出几只小老鼠。这些小老鼠都听他指挥,直立行走,拖着长长的尾巴,可笑地眨巴着一双机灵的像黑珍珠似的眼睛。他对小老鼠可好啦,把它们藏在自己怀里,用嘴含着糖块喂他们,不时地亲吻他们。他令人信服地说: “老鼠是家里聪明的宠物,它非常可爱,家神特别喜欢它!谁养老鼠,家神公公就宠爱谁……” 小茨冈还会用纸牌或钱币变戏法,和孩子们一起玩耍,他的喊叫声比孩子们还高,简直同孩子毫无差别。有一回,他跟孩子们一起玩牌,接连几次被孩子们捉了“傻瓜”,他伤心极了,生气地噘着嘴,就不再玩了。后来,他气呼呼地向我埋怨说: “我知道是他们暗中捣鬼!他们互相使眼色,在桌子底下换牌。这能算是玩牌吗?要是捣鬼,我自己也会,而且不比他们差……” 小茨冈十九岁,比我们四个人的岁数加在一起还大。 在那些节日的夜晚,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这时,外公和米哈伊尔舅舅外出做客去了,雅科夫舅舅披散着满头卷发,抱着吉他来到厨房里,外婆准备了茶水、丰盛的小吃和伏特加酒,绿色的玻璃酒瓶底部有手工雕刻的红花。小茨冈打扮的漂漂亮亮,像陀螺似的旋转着走进来。格里戈里师傅进屋的时候侧着身,轻手轻脚,那幅墨镜的玻璃镜片闪闪发光。麻脸保姆叶夫根尼娅也来了,他的脸红红的,体态胖大,像一只大坛子,她天生一对狡猾的眼睛,嗓音很洪亮。有时候,圣母升天教堂的那个长头发执事,还有一些像梭鱼和鲶鱼一样面色阴郁、行迹可疑的人,也来参加我们的节日晚会。 人们先是大吃大喝,只听见呼哧呼哧的喘气声,然后给孩子们分发节日礼物,再给每人一小杯甜果子酒,接着,热闹而又奇特的娱乐活动就渐渐开始了。 雅科夫舅舅小心翼翼地调着吉他,调好之后,每次都说一句: “喂,诸位,我的演奏现在开始!” 说罢,他抖了抖满头的卷发,躬身抱着吉他,象公鹅似的伸长了脖子,他那张无忧无虑的圆脸仿佛在昏睡似的,他那双生动的、令人难以捉摸的眼睛在一层油雾里变得暗淡无光,他轻轻地扶弄着琴弦,弹起令人陶醉而又令人奋起的乐曲。 雅科夫弹奏的乐曲迫使人们安静下来,全场的气氛颇为紧张。曲子象一条湍急的山溪,从远方奔涌而来,浸透着地板和墙壁,激荡着人们的心,使人产生一种古怪的感觉,一种淡淡的哀愁和不安。倾听这音乐,你的怜悯之心会油然而生,你会怜悯所有的人,也怜悯自己。大人也都变得像孩子一样,大家做在那里屏息不动,一声不响,陷入沉思默想之中。 米哈伊尔舅舅的儿子萨沙听得最为着迷,一幅紧张的神气,一直朝雅科夫探着身子,目不转睛地望着吉他,呆呆地张着嘴,口水从嘴角流下来。有时他听得出神,不小心从椅子上掉下来,连忙用两手撑着地板。这是他干脆坐在地板上,瞪着一双呆滞的眼睛,继续听下去。 大家屏息静气地听着,如醉如痴。只有茶炉在低声欢唱,但这并不防碍人们谛听如怨如诉的吉他声。透过两扇四四方方的小窗,可以看见秋夜黑暗的夜空,时而有人轻轻敲打小窗。桌子上点着两只蜡烛,像长矛似的尖尖的烛焰金灿灿的,轻轻晃动着。 雅科夫舅舅的演奏更加投入了。他仿佛在酣睡,紧紧地咬着牙,只有两只手在单独活动:右手弯曲的手指在深色的吉他腹板上飞快地颤动,宛如一只鸟在扑棱着翅膀拼命挣扎,左手指在琴弦上急速地上下滑动。 他多喝了几杯酒,几乎每次都要用他那难听的、尖细的嗓子唱那冗长的歌谣: 要是雅科夫能变条狗, 从早到晚他叫不休: 噢哟哟,我好寂寞呀! 噢哟哟,我好发愁! 小修女,街上走; 老乌鸦,站墙头。 噢哟哟,我好寂寞呀! 蟋蟀在灶间叫不够, 吵得蟑螂们昏了头。 噢哟哟,我好寂寞呀! 一个乞丐晾晒包脚布, 另一个乞丐就来偷! 噢哟哟,我好寂寞呀! 是啊,哎,我好发愁! 这支歌谣听得我痛苦极了,当雅科夫舅舅唱到那两个乞丐的时候,我实在忍耐不住,伤心地痛哭起来。 小茨冈听音乐的时候,也和大家一样,全神贯注,他把手指插进乌黑的头发里,眼睛盯着屋角,鼻子里发出轻轻的呼噜声。有时他突然叫起来,惋惜地说: “上帝啊,要是给我一副好嗓子,我也来唱一个!” 外婆这时叹着气说: “好啦,雅沙,你弹得让人心里难受!凡尼亚,你来给大家跳个舞吧……” 有时候,外婆的请求不是马上能够得到满足的,不过乐师往往是忽然用手掌按住琴弦,停一秒钟,然后握起拳头,往地板上重重地一甩,仿佛把一件既无形又无声的东西从自己身上甩掉,神气活现地喊道: “扔掉忧愁和烦恼吧!凡尼卡,出场!” 小茨冈捋了捋逢乱的头发,拉了拉那件橘黄色衬衫,像踩着钉子似的小心翼翼地走到厨房中央,他那黑黑的面颊泛起红晕,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请求到: “只是你的节拍要快一点,雅科夫·瓦西里奇!” 于是雅科夫像发疯似的弹起吉他,小茨冈在厨房中央旋转着,仿佛浑身着了火,踏着小碎步,靴跟敲击地板,震得桌子上和橱柜里的餐具哗哗响,一会儿,他又张开双臂,恰如雄鹰展翅,两腿舞的飞快,简直看不出他在迈步;他忽然尖叫,或往下蹲,像一只金色的雨燕飞来飞去,他的丝绸衬衫金光闪闪,颤抖着,浮动着,映照着周围的一切。 小茨冈忘情地跳着,毫无倦意。看来,如果现在打开门让他到外面去跳,他会沿着大街一直跳下去,跳遍全城……” “横穿一次!”雅科夫舅舅用脚打着拍子,喊道。 接着他尖利地吹了一声口哨,用挑逗的声音喊了几句插科打诨的调皮话: 哎嗬哟!我这双破草鞋呀, 扔了怪心疼, 要是没有这双破草鞋呀, 我早就把老婆孩子扔! 坐在桌子四周的人们全身颤动着,有时象被火烧着似的,尖声喊叫着。留大胡子的师傅不时拍打自己光秃秃的头,嘴里低声念叨着什么。有一次,他朝我俯下身来,柔软的大胡子盖住了我的肩头,像对大人似的凑近我的耳朵小声说: “列克赛·马克西梅奇,要是你父亲还活着,请他到这里来,他会跳的更红火!他是个快乐开朗的人,喜欢逗人乐。你还记得他吗?” “记不得了。” “记不得了?他常常和你外婆跳舞,你等一下!” 老师傅说着站起身来,他个子很高,脸色像圣像似的,显得疲惫不堪。他向我外婆鞠一躬,用异常深沉的声音请求道: “阿库里娜·伊凡诺夫娜,劳您的大驾,给大伙儿跳个舞吧!就像您过去跟马克西姆·萨瓦杰耶维奇那样,跳个舞,让我们高兴高兴吧!” “你说什么,亲爱的,你说什么,格里戈里·伊凡内奇先生?”外婆向后缩着身子,面带微笑地说:“我那里会跳舞呀!我就会逗人发笑……” 可是大家不放过她,齐声请求她,这时她像年轻人似的“霍”地一声站起身来,整了整裙子,挺直身子,仰起他那笨大的头,在厨房里跳起舞来,边跳边喊: “好哇,你们尽情地笑吧!喂,雅沙,你给换一个曲子!” 雅科夫舅舅一跃而起,全身挺直,两眼微闭,缓缓地弹奏起来。小茨冈停了一下,跳到外婆跟前,半蹲着身子,围绕着外婆跳,而外婆舒展双臂,轻轻地跳着,她的两脚在地板上无声地滑动,仿佛在空中漂浮着,他扬着眉毛,那双乌黑的眼睛望着远方。我觉的,外婆的样子很滑稽,忍不住“噗哧”一笑。格里戈里师傅立刻伸出一个指头严厉地制止我,所有在场的大人也都用责备的目光扫了我一眼。 “别再跺脚了,伊凡!”格里戈里师傅讥笑地说,小茨冈很听话,立刻跳到旁边,在门槛上坐下来。这时保姆叶夫根尼娅提起嗓子唱起来,她的嗓音不高,但清脆悦耳: 绣花姑娘哟,真可怜, 一个礼拜她要绣六天, 累的她腰酸腿又疼哟, 哎哟哟,忙的她整天不得闲! 外婆不跳了,仿佛在低声讲述什么。这时她轻轻地走来走去,身子摇晃着,若有所思,有时手搭凉棚朝四下里瞧瞧,整个胖大的身躯在优柔地摇动,脚步迟缓,小心翼翼。她停下来,忽然被什么东西吓了一跳,脸哆嗦了一下,皱了皱眉,脸上立刻浮现出和蔼可亲的微笑。她朝旁边躲了躲,伸出一只手,恭恭敬敬地给人让路。然后她垂下头,屏息静气,脸上的笑容更加迷人,她仔细听了听乐曲,忽然间,她迈开舞步,像旋风似的旋转起来,整个身子显得更加匀称,身材也显得更高大了。此时此刻,她奇迹般地恢复了青春,变的漂亮、可爱,优美动人的舞姿紧紧地吸引着人们的视线! 叶夫根尼娅用深沉、洪亮的嗓音唱道: 好容易熬到礼拜天, 做完午祷就去舞翩翩。 她最后一个回家转呀, 真可惜,美妙的节日实在短! 外婆跳完之后,回到茶炉旁边,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大家都夸她的舞跳的好,而她理了理头发,说: “你们算了吧!真正会跳舞的女子你们还没见过呢。在我们巴拉罕纳城,曾经有一个姑娘,我不记得她是谁家的姑娘,叫什么名字了,看她跳舞,有些人会高兴得流泪!只要你看她一眼就够幸福的了,别的什么都不需要了!我非常羡慕她,真是惭愧!” “歌唱家和舞蹈家,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保姆叶夫根尼娅严肃地说,这时她又唱起有关大卫王的歌儿,而雅科夫舅舅搂抱着小茨冈,对他说: “你要是能在酒馆里跳舞就好了,人们看了你的舞蹈会着迷的!……” “我想有一副好嗓子!”小茨冈用抱怨的口吻说,“要是上帝给我一副好嗓子,我呀,先唱十年,然后就去当修士!” 大家都喝了不少酒,格里戈里的酒量特大。外婆一杯接一杯地给他到酒,一面警告他说: “格里沙,你要当心呢,再喝下去,你的眼睛会喝瞎的!” 格里戈里满不在乎地回答说: “那就喝瞎好啦!这双眼睛我也用不着啦,什么世面咱没见过呢……” 他虽然没有喝醉,可是话越来越多,几乎说的都是我父亲的事: “马克西姆·萨瓦杰耶维奇是我的好朋友,他真是个心胸宽广的人……” 外婆连声叹息地附和说: “是啊,他是上帝的好孩子……” 这一切都非常有意思,深深地吸引着我,令我不安,这一切流露着淡淡的哀愁,悄悄地,无休止地侵扰着我的心。在人们身上,哀愁和欢乐同在,无法分开,有时莫名其妙地相互交替着,变幻无常,令人难以捉摸。 有一次,雅科夫舅舅喝了酒,并没有完全喝醉,就动手撕自己的衣服,疯狂地揪自己的头发和稀疏的淡黄色胡子,揪自己的鼻子和下垂的嘴唇。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号啕大哭,泪流满面。“这是为什么?” 他在自己脸上、额头上和胸脯上捶打着,大声哭诉着: “我是恶棍,下流坯,我是不要脸的东西!” 格里戈里也在大声号哭: “说的对,骂得好!……” 我外婆也带着醉意,他抓住儿子一只手,劝解说: “得了,得了,雅沙,上帝知道该怎么教导人!” 外婆喝酒之后,变的更好看了:那双乌黑的眼睛笑眯眯地看着每个人,闪烁着温暖人心的光芒,她挥动头巾扇着通红的脸,用唱歌似的嗓音说: “上帝呀,上帝,一切多么美好啊!哎,你们快瞧瞧吧,一切是多么美好啊!” 这是她的心声,她终生都在发出这样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