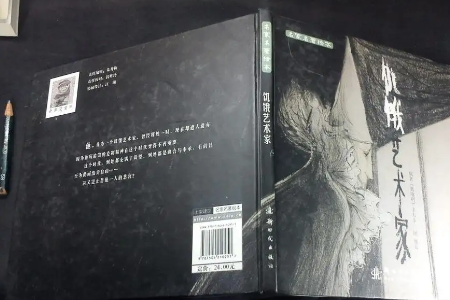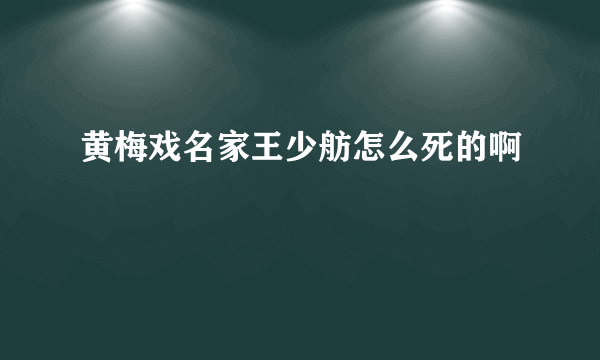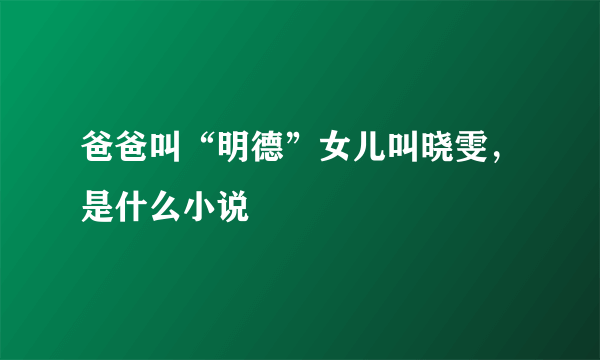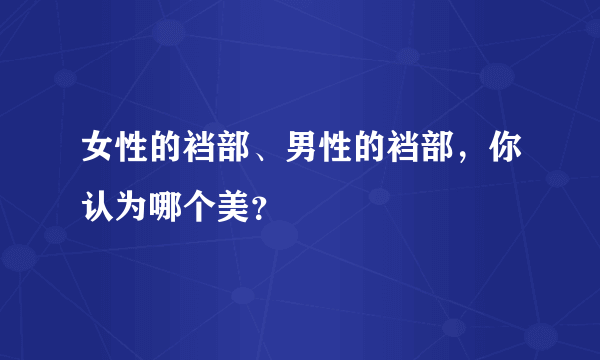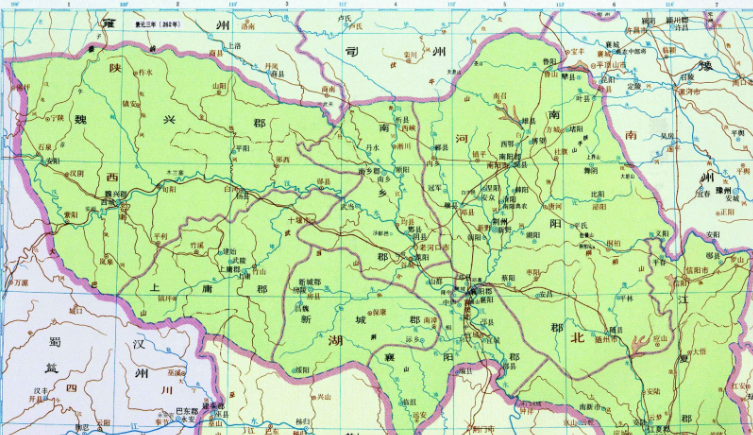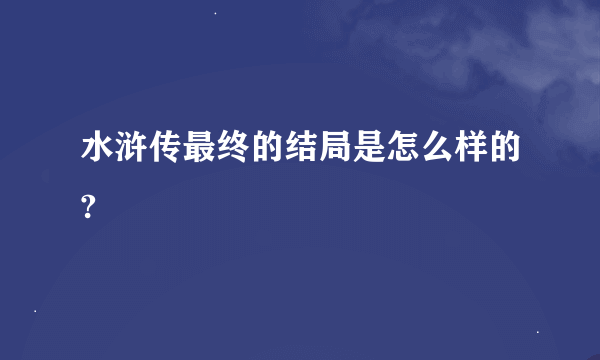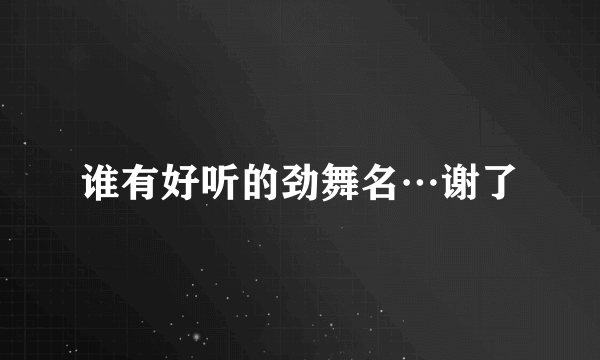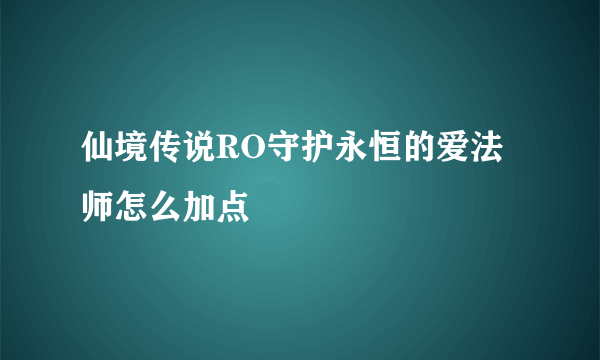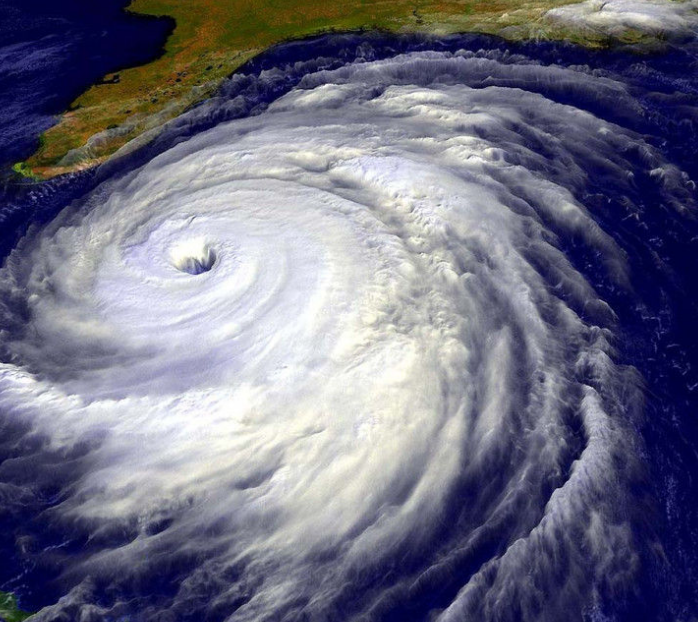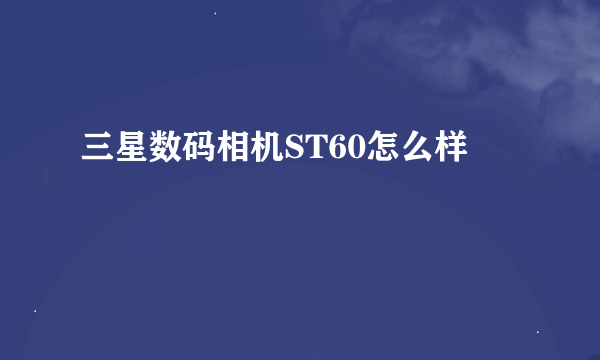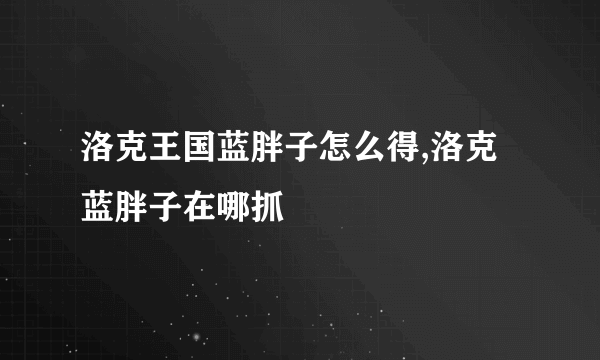求余秋雨短篇散文 求原文、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雪 美丽的雪花飞舞起来了。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也曾见过雪。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可不是飞舞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随着雨点洒下来几颗,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它的颜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点,并不会飞舞。一到地面,它立刻融成了水,没有痕迹,也未尝跳跃,也未尝发出唏嘘的声音,像江浙一带下雪时的模样。这样的雪,在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诚然能感到特别的意味,谈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却总觉得索然。"福建下过雪",我可没有这样想过。 我喜欢眼前飞舞着的上海的雪花。它才是"雪白"的白色,也才是花一样的美丽。它好像比空气还轻,并不从半空里落下来,而是被空气从地面卷起来的。然而它又像是活的生物,像夏天黄昏时候的成群的蚊蚋(ruì),像春天酿蜜时期的蜜蜂,它的忙碌的飞翔,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粘着人身,或拥入窗隙,仿佛自有它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它静默无声。但在它飞舞的时候,我们似乎听见了千百万人马的呼号和脚步声,大海汹涌的波涛声,森林的狂吼声,有时又似乎听见了儿女的窃窃私语声,礼拜堂的平静的晚祷声,花园里的欢乐的鸟歌声……它所带来的是阴沉与严寒。但在它的飞舞的姿态中,我们看见了慈善的母亲,活泼的孩子,微笑的花儿,和暖的太阳,静默的晚霞……它没有气息。但当它扑到我们面上的时候,我们似乎闻到了旷野间鲜洁的空气的气息,山谷中幽雅的兰花的气息,花园里浓郁的玫瑰的气息,清淡的茉莉花的气息……在白天,它做出千百种婀娜的姿态;夜间,它发出银色的光辉,照耀着我们行路的人,又在我们的玻璃窗上扎扎地绘就了各式各样的花卉和树木,斜的,直的,弯的,倒的。还有那河流,那天上的云… <山居笔记> 酣睡在寒风中 “文革”中有一件小小的趣事,老在我的记忆里晃动。 那时学校由造反派执掌,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清晨全体师生必须出操。其实当时学校早已停课,出完操后什么事也没有了,大家都作鸟兽散,因此,出操是造反派体验掌权威仪的唯一机会。 老师们都是惊弓之鸟,不能不去;像我们这批曾经对抗过造反派、现在已成瓮中鳖而家里又有很多麻烦事的学生也不能不去;只有几个自称“逍遥派”的同学坚持不出操,任凭高间喇叭千呼万唤依然蒙头睡觉。这很损造反派的脸面,于是在一次会上决定,明天早晨,把这几个人连床抬到操场上示众。 第二天果然照此办理,严冬清晨的操场上,呼呼拉拉的人群吃力地抬着几张耸着被窝的床出来了。造反派们一阵喧笑,出操的师生们也忍俊不禁。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难道强迫这些“逍遥派”当众钻出被窝穿衣起床?如果这样做他们也太排场了,简直就像老爷一样。于是造反派头头下令,“就让他们这样躺着示众!”但蒙头大睡算什么示众呢?我们边上操边看着这些床,这边是凛冽的寒风,那边是温暖的被窝,真是让人羡慕死了。造反派头头似乎也觉得情景不对,只得再下一个命令:“示众结束,抬回去!”那些温暖的被窝又乐颠颠地被抬回去了。后来据抬的同学抱怨,这些被抬进抬出的人中,至少有两个从头至尾没有醒过。 由这件往事,我想起很多道理。 示众,只是发难者单方面的想法。如果被示众者没有这种感觉,那很可能是一个享受。世间的惩罚可分直接伤害和名誉羞辱两种,对前者无可奈何,而对后者,地实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一个人要实现对另一个人的名誉羞辱,需要依赖许多复杂条件,当这些条件未能全然控制,就很难真正达到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常受围攻的人名誉未倒,而那些批判专家劳苦半辈子都未能为自己争来任何好名誉的原因了。 让他们站在寒风中慷慨激昂吧,我们自有温暖的被窝,乐得酣睡。抬来抬去,抬进抬出,辛苦了。